当地时间10月7日,诺奖委员会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米歇尔·H·德沃雷(Michel H. Devoret)和约翰·M·马丁尼斯(John M. Martinis)三人,他们因发现了“电路中的宏观量子力学隧穿和能量量子化”而获奖。
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成员埃娃·奥尔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这一获奖成就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使人们能够在更大尺度上研究量子力学世界。
量子计算破冰
三人使用的核心器件是约瑟夫森结:两片超导电极中间隔着一层极薄的绝缘层。处于低温时,电子成对耦合成“库珀对”并以群体方式运动。因为这些库珀对共享统一的量子相位,整个回路的量子态可用一支宏观波函数来描述,仿佛一个整体行动的“单粒子”。
在适当的偏置条件下,电流会被“锁定”在零电压的稳定态中。实验发现,系统能够凭借量子隧穿越过势垒并突然切换到出现电压的状态——这就是“宏观量子隧穿”。随后通过微波激发进行谱学测量,人们观测到能级是离散且可逐级激发的,表明这一宏观电路的行为完全受量子力学规律支配。
实际上,这类宏观量子态为利用粒子微观世界的现象开展实验提供了新可能,因为此类 “人工单粒子”可模拟其他量子系统,帮助研究者理解这些系统特性。三位诺奖得主的实验不仅具有重大科学意义,也将量子力学从理论与微观世界带进了可工程化的电路体系。
量子力学在1925年诞生,今年正值百年。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主席奥勒·埃里克松颁奖当天表示,百年来量子力学不断带来新的惊喜,它大有用处,为数字技术提供了基础。
近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多次青睐量子领域:2012年,塞尔日·阿罗什与大卫·J·温兰因“对单个量子系统的测量与操控”的开创性方法获奖;当年新闻稿并指出,或许量子计算机会在本世纪像上一世纪的经典计算机那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2022年,阿兰·阿斯佩、约翰·F·克劳泽与安东·蔡林格因纠缠光子与贝尔不等式实验获奖,被官方概括为“开创量子信息科学”。
对比经典计算机,被称为“量子计算机”的新概念受到行业广泛重视。
198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就提出了“量子计算机”的概念,此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量子计算机的研发一直停留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但最近两年,量子计算机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与大众视野中。
2024年12月,谷歌推出全新的量子芯片——Willow(共105个量子比特),在物理学界和AI圈掀起了海啸般的巨震,美股量子概念股暴涨。
现有计算机计算体系采用的是经典计算,以0和1的比特按确定性逻辑门逐步演化来处理信息;而量子计算则反其道行之,借助量子比特的叠加与纠缠,让多种可能态并行演化,直接模拟包括分子化学与新材料在内的大量量子体系的本征规律。理论上,量子计算进行某些类型计算的速度可以比传统计算机快数十亿倍。
量子商用路径
因为量子计算在通信、金融、医疗、生物、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都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诸多国家与科技巨头纷纷加入了这场量子计算研发竞赛。美国、日本等先后制定了国家层面的量子计算发展规划,谷歌、英伟达、IBM、微软等科技巨头积极推进研究。
在中国,本源悟空、玻色量子、国盾量子(688027.SH)等公司在量子计算领域也耕耘已久。
量子计算要走向可规模化商业化,面临数个关口:首先,要把量子比特(qubit)做得“稳而准”, 保持叠加态,在长相干时间与高门保真下实现可用的量子纠错,降低从物理比特到逻辑比特的巨大开销;其次,硬件与控制系统需工程化扩展,从几十到成千上万比特的规模,解决低温与光学控制、互连与封装的良率与可重复性;最后,应用端要找到可验证的量子优势场景,将量子—经典混合算法嵌入真实工作流。
不过,解决上述问题仍是困难重重,各路线都在试错阶段。以保持量子系统中保持一个量子比特的叠加态为例,就必须尽可能保证量子比特不与环境发生不可控耦合。任何微弱的“扰动”,无论是温度闪动、电磁场波动、材料缺陷、杂质还是外部线路的信号串扰,都可能成为“噪声源”,把量子信息“泄露”出去,使系统失去相干性,这种现象被称为“退相干”。
目前全球推进量子计算机的技术路线包括超导量子、离子阱、光量子、拓扑量子等多个技术路线。
其中,超导量子计算机是利用超导材料极低温形成的库珀电子对作为量子比特,再通过微波脉冲操控,代表厂商包括 IBM、谷歌、国盾量子、本源量子等,是量子计算机主流路线。但该路线需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以及量子比特相干时间较短,是主要挑战。
颇值得注意的是拓扑量子,这是一种较新的技术路线。
今年2月,微软宣布取得量子计算的“突破性进展”,为了制造量子芯片,其研究人员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拓扑导体”。微软表示,该拓扑导体利用了一种被称为“拓扑超导”的物质状态,“拓扑超导”既不是固体、液体也不是气体的材料,过去只存在于理论中。这种拓扑量子计算机理论上高度抗干扰,错误率低,微软还表示正在开发的量子芯片,使其能够容纳100万个量子比特,不过,“拓扑导体”材料目前仍制备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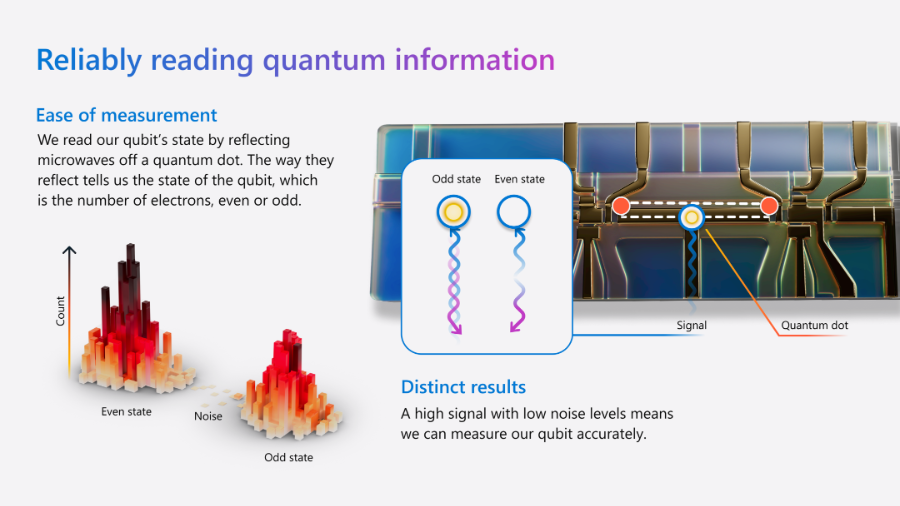
(微软公司宣布推出全球首款基于拓扑量子比特的量子处理器,该量子处理器基于拓扑导体材料构建。图片来源:微软)
多条技术路线并进、相互竞争,本身也说明量子技术仍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因此,即便实验频传捷报,业界仍难判断:这些突破能否在数年内转化为可商用的量子计算机,抑或仍需十年甚至更久。
实际上,在知名IT顾问咨询公司Gartner过去几年发布的新兴技术炒作周期曲线中,量子计算技术已在“创新触发期”(Innovation Trigger)盘桓多年,一直未进入下一个周期。
由于技术方向尚未收敛,资本侧趋于谨慎,更多投资者选择观望。真正值得期待的,是能显著拉近“可用”与“可卖”距离的实质性进展,以及某个类似生成式AI浪潮的“ChatGPT时刻”——一旦到来,它或将像过去两年AI行业那样点燃并加速量子计算的繁荣。
资本激情萌动
尽管诺奖进一步肯定了量子力学的潜力、科技巨头也在持续加码,但从资本市场看,量子领域仍处在高投入、长周期的“烧钱”阶段。
多家机构判断其潜在市场空间巨大。摩根大通分析师Samik Chattejee在最新量子计算报告中预计,量子计算将受益于持续资本投入,仅2025年全球公共投资或将达到450亿美元。
海外资本市场方面,当前已上市的量子计算相关公司包括IonQ、Quantum Computing、D-Wave Quantum与Rigetti Computing,从体量上看均属与量子计算密切相关的小型股。且财务表现仍显薄弱,上述公司上市时间不长,至今均未实现盈利。其中 IonQ 相对最成熟,但其2024年销售额也仅为4310万美元。
同时,鉴于这些公司深耕的仍是尚未被商业验证的技术赛道,它们本质上依旧是高投机标的。如今年2月微软披露“突破性进展”后,板块情绪提振,消息发布不久,D-Wave午盘一度涨逾7%,Rigetti Computing亦接近4%的涨幅。
随后,量子计算股今年的股价走向愈加“疯狂”,Quantum Computing自3月14日低点4.37美元/股上涨至7月11日高点21.88美元/股,累计涨幅304.41%;截至本月,Quantum Computing在二级市场仍整体上行,13日收盘报21.46美元/股。另据盘面表现,美股量子计算板块近半年集体走强:IonQ六个月大涨近223%,D-Wave Quantum亦涨逾478%。
对于此类公司异常的股价涨幅变动,瑞穗证券美国公司董事总经理Daniel ORegan的判断颇为直白:这是一场“炒作中的炒作”。
不少公司几乎没有收入,买入者多是在编织下一个风口的想象。
相较之下,国内量子科技上市公司数量更少,除已上市的国盾量子外,国仪量子、本源量子正处于上市辅导阶段,更多创业公司仍在融资推进中。总体来看,技术路径未定与商业模式待证的双重不确定性仍在,但产业链的“耐心资本”与技术里程碑正不断累加。
今年以来,国内量子计算赛道投融资活跃。截至三季度末,就有14家企业合计完成16轮融资,覆盖天使到C轮不等。
其中,中科酷原与玻色量子均完成两轮融资:前者同时布局原子量子计算与量子精密测量,核心产品包括“汉原1号”原子量子计算机、便携式原子量子重力仪等;后者专注光量子计算,2025年4月发布新一代具备约1000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相干光量子计算机真机,并在苏州、深圳、南京等地建设实验室,面向人工智能、生物制药、金融、通信、能源等领域开展场景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