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策略
◆
◆
发表于 2025-04-29 15:44:53
发布于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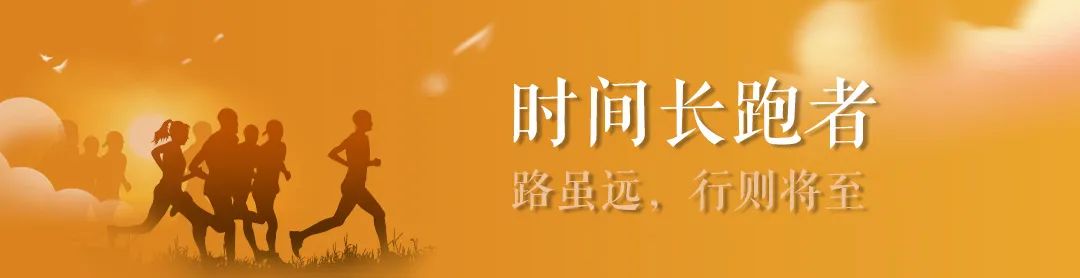
编者按

今年是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60周年。60年来,“股神”巴菲特以价值为锚,穿越经济周期的迷雾,创造了60年暴赚5.5万倍的财富神话。在2025年巴菲特股东大会来临之际,腾讯财经联合自选股发起“秩序与周期:价值投资60年”系列策划,本期内容邀请重阳投资合伙人舒泰峰撰文,还原巴菲特选股的三个重要阶段及其背后的商业逻辑变迁。
 现年94岁的巴菲特再一次“封神”。北京时间2月22日9点,伯克希尔哈撒韦官网公布了2024年年度报告,以及一份沃伦·巴菲特每年亲自撰写的致股东信,其中披露,到2024 年底,巴菲特手中的现金再次创纪录地达到3342亿美元,高于第三季度末的3252亿美元。 除了经营性现金流的贡献之外,现金的主要源头还来自2024年伯克希尔将流通股持仓从年初的3540亿美元降至年末的2720亿美元,减持的标的包括巴菲特的“心头好”——苹果公司。2024年全年,伯克希尔累计减持苹果近67%,从9.05亿股降至3亿股。大幅减持之后,截止2024年第四季度,苹果仍以28%的权重稳居巴菲特第一大持仓。 世人通常刻板地把巴菲特的投资策略等同于买入并长期持有,其实这是对巴菲特的严重误读,尽管巴菲特的一些经典持仓的确持有时间可长达数十年,比如喜诗糖果、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富国银行等,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巴菲特的适时而动、灵活机变同样精彩绝伦。 经过这次仓位减持,目前巴菲特的股票仓位大致在50%左右,同时掌握着一半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等待机会成熟时抄底市场,可以预见巴菲特的财富神话还将续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了仓位的适时而动,看巴菲特数十年核心重仓股的变化更能体会到他根据产业趋势变迁而变化的调整能力和持续迭代进化的学习能力。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在投资的理念上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转变,也就是从最早格雷厄姆式的“捡烟蒂”投资方式(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平庸公司)到后期受芒格影响而调整为“以合理价格购买优秀公司”,但是如果结合产业趋势和商业模式的变化,事实上巴菲特投资可以划分为更细的三个阶段。罗伯特·哈格斯特朗研究巴菲特超过30年,他在《终极金钱心智》这本书很好地剖析了巴菲特的这一变化。 第一阶段:工业时代下的“捡烟蒂”投资阶段 “捡烟蒂”投资法由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核心是以极低价格(如价格低于净资产的2/3)买入被市场忽视的公司。由于买入价格极低,所以这种方法的安全边际很高。即使公司状况恶化,也能通过清算资产保障本金安全,如同捡拾被丢弃但仍可吸一口的烟蒂。 为什么格雷厄姆会提出这样一种投资方法,这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方能理解。“捡烟蒂”投资法形成于20世纪20—40年代,当时正值大萧条期间。1929年美股崩盘后,大量公司股价远低于其账面价值,甚至低于净流动资产,市场极度悲观。格雷厄姆本人因杠杆投资在1929年亏损近70%,这段经历促使他变得更为保守。 这一投资方法的形成也与经济结构相关。当时的美国经济以重资产为主:早期工业时代的企业(如铁路、制造业)拥有大量有形资产,公司的投资主要是在财产、厂房和设备上。厂房由有形的建筑物组成,主要是砖石和砂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巴鲁克·列夫和卡尔加里大学哈斯凯恩商学院的阿努普·斯里瓦斯塔瓦两位教授指出,当时的会计规则规定,这些有形资产的资本化,必须充分反映在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折旧费用数据上。与此相对应,放眼整个美国企业界,大多数公司的估值主要由其账面价值来定义。根据统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市公司的市净率中值一直徘徊在1倍左右。这样的背景为“捡烟蒂”式投资方法提供了适用的土壤。 巴菲特早年严格遵循老师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碰到了不少“价值陷阱”。巴菲特对此做过自嘲:“以短线的心态投资农场设备制造公司、三流的百货公司和新英格兰纺织制公司,这些投资在经济上给我带来的教训是对我的惩罚。” 巴菲特提到的农场设备制造公司指的是登普斯特农机制造公司,三流的百货公司指的是霍克希尔德·科恩,纺织制造公司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尤其是 登普斯特农机制造公司,由于公司效率低下,当时不到30岁年轻气盛的巴菲特接管后进行了严厉的成本削减,包括关闭部分生产线、解雇大量工人。这导致公司所在地的农民和工人强烈不满,因为许多家庭依赖这家企业谋生。巴菲特的行为一时被媒体形容为“华尔街资本家压榨小镇企业”,搞得狼狈不堪。 “捡烟蒂”投资法越来越暴露出其时代的局限性。 第二阶段,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 巴菲特投资方式的重大转变开始于对喜诗糖果的投资,这桩买卖是由芒格推动的。1972年,伯克希尔哈旗下的蓝筹印花公司与喜诗糖果创始人家族谈判整体收购。对方要价为4000万美元,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上的1000万美元现金。喜诗糖果账面上的有形资产只有800万美元,年度税前利润为400万美元。芒格认为这笔交易很合算,但巴菲特却不太肯定。他指出,这个要价是有形资产的3倍,如果换作他的老师本·格雷厄姆,肯定不会同意的。于是巴菲特还价到2500万美元,但他仍然认为自己可能出价过高了。 事后看,当年巴菲特并没有为喜诗糖果支付过多的钱。事实上,喜诗糖果是有史以来给伯克希尔带来回报最高的公司之一。从1972年到1999年喜诗糖果产生的内部回报率(IRR)达到了惊人的32%。2014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报显示,喜诗糖果公司给伯克希尔带来了19亿美元的税前利润,而仅仅增加了4000万美元的额外投资。 从喜诗糖果的投资开始,用他自己的自嘲来形容,巴菲特完成了“从猩猩到人”的伟大一跃,此后他将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等优质公司纷纷收入囊中,构建了一个优质企业的珍藏馆。我们来看看更为经典的对可口可乐的投资。可口可乐是巴菲特的非卖品,伯克希尔目前拥有4亿股可口可乐股票,自1988年第一笔投资以来,从未卖出过1股。 回到1988年,如果按照静态的账面价值,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时付出了一定的溢价。当时可口可乐的PE是15倍,股价是现金流的12倍,分别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出30%和50%。巴菲特支付了5倍的市净率,这样只有6.6%的收益率,相对于长期国债9%的收益率,似乎并不具有吸引力。 但是巴菲特认为,股票的价格说明不了价值。可口可乐的价值和其他企业一样,取决于未来公司存续期内,所有预期股东盈余的折现。 1988年,可口可乐公司股东盈余为8.28亿美元,美国30年期国债的利率(无风险利率)是9%。以1988年的盈余,使用9%作为贴现率,可以算出公司价值为92亿美元。当巴菲特购买可口可乐时,公司的总市值为148亿美元。 按照这种静态的计算方式看,巴菲特买高了,但是别忘了,92亿美元的估值是基于当时盈余的计算而忽视了可口可乐公司未来成长的空间。其实哪怕用5%的最保守增长率的来计算,公司也至少值207亿美元。所以巴菲特的这笔投资仍然具有很好的安全边际。 在另一次演讲中,巴菲特使用了更为简单的相对估值方法。他是这么考虑的:如果要在几年内完全复制出可口可乐这个品牌,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最后他和芒格得出的结论是:就算这个地球上最好的营销团队,想要复制可乐的品牌,1000亿美元都办不到。而当时可口可乐的公司市值不超过200亿美元。一个仅仅品牌价值就超过1000亿的公司,用不到200亿就可以买到,这当然是桩好买卖。 如果说喜诗糖果是巴菲特投资理念转变后的小试牛刀,那么对可口可乐的投资则是经典案例。巴菲特将自己的投资理念变化归功于芒格的推动,但实际上这背后也反映了美国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商业模式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如果说工业革命以来,对有形资产(财产、厂房和设备)的投资定义了企业的价值,但从这时开始,这些让位于对无形资产的投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版权、商标和品牌。有形资产由实物财产定义,而无形资产由知识产权定义。由于会计准则植根于工业时代,根据会计准则,公司必须立即将所有的无形投资成本化,简而言之,对无形资产的投资不会增加公司的账面价值。尽管对无形资产的投资确实能增加公司的内在价值,但在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方法中并没有提到这些。 还是巴鲁克·列夫和阿努普·斯里瓦斯塔瓦两位教授指出,自1980年以来,美国公司投资于有形资产的资金逐渐减少,投资于无形资产的资金相应增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无形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超过了有形资产的增长率。 上述这些情况,对典型的价值投资者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投资于无形资产的公司必须从当前利润中减去这一成本,同时由于不能将投资金额计入账面价值,反过来又使得其具有高市盈率和高市净率的特征,这使股票显得很昂贵。但是,如果将估值方法从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转变为用调整后的现金流和资本回报率计算所带来的利润,那么从GAAP角度看起来昂贵的公司,实际上可能对具有公司股东心态的投资者而言,就具有了吸引力。 巴菲特看起来放松了对估值的要求,实际上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商业变迁。 第三阶段:从新经济模式下的网络效应中获取价值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他对苹果公司的投资。 巴菲特于2016年开始投资苹果,到2022年对苹果的持仓市值超过1200亿美元,占组合的比重达到40.76%。苹果也热切地回报了巴菲特,为他贡献了1000多亿美元的投资收益。在单只股票上赚取1000多亿美元,这也创造了投资史上的一个奇迹。 众所皆知,巴菲特一直给外界的印象是不愿意投资科技股,直到2013年芒格还说过,全世界都羡慕苹果的成就,但也没有比苹果更不符合伯克希尔想投资的企业标准的。他说,“我们真的非常讨厌必须要创造出全新的、创新的科技,还需要一个接一个不间断。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做不到苹果这样。所以我们也不会去试图进入苹果。” 没想到三年之后的2016年,巴菲特开始大举买入苹果。笔者在《财富善战者说》一书中概括了巴菲特买入苹果的几个理由:首先,苹果虽然具有很强的科技属性,但是它一定程度上是个消费品。其次,他运用菲利普·费雪的“闲聊投资法”,发现苹果的粘性极强。他带曾孙们去吃冰淇淋,看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部手机,年轻人的生活几乎全部围绕苹果手机进行,而一旦苹果推出新品,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更换。苹果公司拥有数以亿计有购买力的用户,他们可以用手机来交易、学习甚至做其它的事情,这俨然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第三,巴菲特非常欣赏苹果CEO蒂姆·库克,甚至不惜称赞他是“伟大的管理者”。他曾在2021年的年度信函中表示:“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将苹果产品的用户视为他的初恋,他的管理风格也让很多人受益。” 库克执掌苹果之后大力推动股票派息和回购。在过去三年里,这家科技巨头每年派息约140亿美元。苹果从2012年3月开始支付季度股息并回购股票。根据标普全球市场财智公司提供的数据,从那以后一直到2021年夏天,苹果已经在股票回购上花费了超过4670亿美元。回购可以减少公司的股票数量,从而提振收益和股价。这是巴菲特非常喜欢的一类投资标的。 苹果还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现金奶牛”。截止2022年第一季度,苹果拥有约2026亿美元的现金储备,远高于与科技公司谷歌(1692亿美元)和微软(1324亿美元)。充沛的现金是苹果可以实施大规模回购和现金分红的基础。所以,如果说乔布斯时期的苹果是一个科技成长型企业,而库克接管之后的苹果则进一步转型为了一家蓝筹股企业。 第四,巴菲特买在苹果的低迷时刻。表面上看2016年并不是什么好的时机。从行业角度,当时恰逢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到达行业天花板,行业开始进入下行的节点。而从苹果本身来看,此时乔布斯已经去世5年,苹果被批评为创意枯竭,当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业绩13年来首次下滑,营收下降13%,净利下滑22%。2016全年苹果年营收为2170亿美元,比前一年下滑9%。 但是巴菲特看到的东西不一样,2016年初,全球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上,苹果份额为62.3%,三星为22.1%。虽然创新不足,但是苹果的市场优势却在不断扩大。这说明通过多年的技术领先,苹果已经实现了可持续的垄断性领导力,它的护城河已经坚不可摧,而盈利的暂时下滑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买入时机。 《终极金钱心智》这本书则为巴菲特购买苹果公司增加了一个商业模式变化的最新背景。如果说巴菲特的第一阶段投资对应的是工业时代的厂房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第二阶段投资是从有形资产转向了对品牌、专利等无形资产,那么他的第三阶段投资则开始关注到了新经济模式下的网络效应及指数化增长。 苹果公司无疑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这符合第二阶段的特征, 同时苹果也是一只新经济类型的股票,苹果的所有产品和服务都使用了苹果的IOS操作系统,一旦产品成为苹果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网络效应就会形成,正向反馈、路径依赖和锚定效应等将创造一个强大的全球特许经营权,因为苹果客户的转换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网络效应背后则藏着旧经济与新经济的深刻分野。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指出,旧经济学更多地是基于物理学,其特征是“平衡”、“理性”,而在新经济学更类似于生物学,认为人是情绪化且不理性的,经济是复杂系统而不是简单系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不是静态的。 在以物理学为标准的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理论中,市场呈现出收益递减状态。收益递减定律是标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其内涵包括,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多增加一个因素,即要求,就会在某个时点上降低单位生产的增量回报。换句话说,收益递减定律是指达到某一点后,所获得的经济回报水平相对于所投资的资金而言,会下降。 然而,复杂经济学认为,有些公司注定不会受长期收益递减定律的影响。根据阿瑟的观点,有一些公司的经济回报会继续增长,他解释说:“加速回报,是指那些领先的会进一步领先,而那些失去优势的会进一步落后。”收益递减是旧的实体经济的一个特征,与此同时,“加速回报正在成为新经济,也就是知识型产业的特征。” 加速回报在网络效应常见的特定技术领域中尤为显著。网络效应是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某个产品或服务,其价值会有所增加的现象。所以在新经济条件下,一旦某个网络达到50%的市场份额,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坚不可摧的实体。创造数亿美元利润的公司往往能有数十亿元的市值,而推动这些所需的资本仅仅是工业革命时代所需资本的一部分而已。 巴菲特自己并没有从这个角度阐述过投资苹果的理由,不过哈格斯特朗还是认为对苹果的投资代表了巴菲特跨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投资价值的完美投资案例。 在2019年伯克希尔年会上,芒格指出,巴菲特愿意投资苹果对伯克希尔来说是一个好兆。芒格打趣道:“要么是你发疯了,要么就是你在学习,我更喜欢学习的这种解释。” 的确,永不放弃学习可能才是我们最需要向巴菲特学习的地方。哈格斯特朗也感慨,研究巴菲特的最大回报之一,是观察他作为投资者在过去65年里是如何发展的,从价值投资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现在再到第三阶段。“很少有投资者能从第一种方法进化到第二种方法,更不用说第三种方法了。要想在一个市场周期中取得成功,需要灵活的头脑、合适的投资气质以及持续学习的强烈愿望。这是金钱心智运作的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巴菲特60多年漫长职业生涯表面波澜不惊的背后实际上暗藏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惊人迭代进化,很多人批评他错过了新经济,实际上他并没有缺席任何一次重大的商业模式变迁,甚至比任何人都抓住了更多。 (舒泰峰 重阳投资合伙人,财经作家,著有《财富是认知的变现》、《财富善战者说》等)
现年94岁的巴菲特再一次“封神”。北京时间2月22日9点,伯克希尔哈撒韦官网公布了2024年年度报告,以及一份沃伦·巴菲特每年亲自撰写的致股东信,其中披露,到2024 年底,巴菲特手中的现金再次创纪录地达到3342亿美元,高于第三季度末的3252亿美元。 除了经营性现金流的贡献之外,现金的主要源头还来自2024年伯克希尔将流通股持仓从年初的3540亿美元降至年末的2720亿美元,减持的标的包括巴菲特的“心头好”——苹果公司。2024年全年,伯克希尔累计减持苹果近67%,从9.05亿股降至3亿股。大幅减持之后,截止2024年第四季度,苹果仍以28%的权重稳居巴菲特第一大持仓。 世人通常刻板地把巴菲特的投资策略等同于买入并长期持有,其实这是对巴菲特的严重误读,尽管巴菲特的一些经典持仓的确持有时间可长达数十年,比如喜诗糖果、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富国银行等,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巴菲特的适时而动、灵活机变同样精彩绝伦。 经过这次仓位减持,目前巴菲特的股票仓位大致在50%左右,同时掌握着一半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等待机会成熟时抄底市场,可以预见巴菲特的财富神话还将续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了仓位的适时而动,看巴菲特数十年核心重仓股的变化更能体会到他根据产业趋势变迁而变化的调整能力和持续迭代进化的学习能力。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在投资的理念上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转变,也就是从最早格雷厄姆式的“捡烟蒂”投资方式(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平庸公司)到后期受芒格影响而调整为“以合理价格购买优秀公司”,但是如果结合产业趋势和商业模式的变化,事实上巴菲特投资可以划分为更细的三个阶段。罗伯特·哈格斯特朗研究巴菲特超过30年,他在《终极金钱心智》这本书很好地剖析了巴菲特的这一变化。 第一阶段:工业时代下的“捡烟蒂”投资阶段 “捡烟蒂”投资法由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核心是以极低价格(如价格低于净资产的2/3)买入被市场忽视的公司。由于买入价格极低,所以这种方法的安全边际很高。即使公司状况恶化,也能通过清算资产保障本金安全,如同捡拾被丢弃但仍可吸一口的烟蒂。 为什么格雷厄姆会提出这样一种投资方法,这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方能理解。“捡烟蒂”投资法形成于20世纪20—40年代,当时正值大萧条期间。1929年美股崩盘后,大量公司股价远低于其账面价值,甚至低于净流动资产,市场极度悲观。格雷厄姆本人因杠杆投资在1929年亏损近70%,这段经历促使他变得更为保守。 这一投资方法的形成也与经济结构相关。当时的美国经济以重资产为主:早期工业时代的企业(如铁路、制造业)拥有大量有形资产,公司的投资主要是在财产、厂房和设备上。厂房由有形的建筑物组成,主要是砖石和砂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巴鲁克·列夫和卡尔加里大学哈斯凯恩商学院的阿努普·斯里瓦斯塔瓦两位教授指出,当时的会计规则规定,这些有形资产的资本化,必须充分反映在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折旧费用数据上。与此相对应,放眼整个美国企业界,大多数公司的估值主要由其账面价值来定义。根据统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市公司的市净率中值一直徘徊在1倍左右。这样的背景为“捡烟蒂”式投资方法提供了适用的土壤。 巴菲特早年严格遵循老师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碰到了不少“价值陷阱”。巴菲特对此做过自嘲:“以短线的心态投资农场设备制造公司、三流的百货公司和新英格兰纺织制公司,这些投资在经济上给我带来的教训是对我的惩罚。” 巴菲特提到的农场设备制造公司指的是登普斯特农机制造公司,三流的百货公司指的是霍克希尔德·科恩,纺织制造公司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尤其是 登普斯特农机制造公司,由于公司效率低下,当时不到30岁年轻气盛的巴菲特接管后进行了严厉的成本削减,包括关闭部分生产线、解雇大量工人。这导致公司所在地的农民和工人强烈不满,因为许多家庭依赖这家企业谋生。巴菲特的行为一时被媒体形容为“华尔街资本家压榨小镇企业”,搞得狼狈不堪。 “捡烟蒂”投资法越来越暴露出其时代的局限性。 第二阶段,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 巴菲特投资方式的重大转变开始于对喜诗糖果的投资,这桩买卖是由芒格推动的。1972年,伯克希尔哈旗下的蓝筹印花公司与喜诗糖果创始人家族谈判整体收购。对方要价为4000万美元,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上的1000万美元现金。喜诗糖果账面上的有形资产只有800万美元,年度税前利润为400万美元。芒格认为这笔交易很合算,但巴菲特却不太肯定。他指出,这个要价是有形资产的3倍,如果换作他的老师本·格雷厄姆,肯定不会同意的。于是巴菲特还价到2500万美元,但他仍然认为自己可能出价过高了。 事后看,当年巴菲特并没有为喜诗糖果支付过多的钱。事实上,喜诗糖果是有史以来给伯克希尔带来回报最高的公司之一。从1972年到1999年喜诗糖果产生的内部回报率(IRR)达到了惊人的32%。2014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报显示,喜诗糖果公司给伯克希尔带来了19亿美元的税前利润,而仅仅增加了4000万美元的额外投资。 从喜诗糖果的投资开始,用他自己的自嘲来形容,巴菲特完成了“从猩猩到人”的伟大一跃,此后他将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等优质公司纷纷收入囊中,构建了一个优质企业的珍藏馆。我们来看看更为经典的对可口可乐的投资。可口可乐是巴菲特的非卖品,伯克希尔目前拥有4亿股可口可乐股票,自1988年第一笔投资以来,从未卖出过1股。 回到1988年,如果按照静态的账面价值,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时付出了一定的溢价。当时可口可乐的PE是15倍,股价是现金流的12倍,分别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出30%和50%。巴菲特支付了5倍的市净率,这样只有6.6%的收益率,相对于长期国债9%的收益率,似乎并不具有吸引力。 但是巴菲特认为,股票的价格说明不了价值。可口可乐的价值和其他企业一样,取决于未来公司存续期内,所有预期股东盈余的折现。 1988年,可口可乐公司股东盈余为8.28亿美元,美国30年期国债的利率(无风险利率)是9%。以1988年的盈余,使用9%作为贴现率,可以算出公司价值为92亿美元。当巴菲特购买可口可乐时,公司的总市值为148亿美元。 按照这种静态的计算方式看,巴菲特买高了,但是别忘了,92亿美元的估值是基于当时盈余的计算而忽视了可口可乐公司未来成长的空间。其实哪怕用5%的最保守增长率的来计算,公司也至少值207亿美元。所以巴菲特的这笔投资仍然具有很好的安全边际。 在另一次演讲中,巴菲特使用了更为简单的相对估值方法。他是这么考虑的:如果要在几年内完全复制出可口可乐这个品牌,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最后他和芒格得出的结论是:就算这个地球上最好的营销团队,想要复制可乐的品牌,1000亿美元都办不到。而当时可口可乐的公司市值不超过200亿美元。一个仅仅品牌价值就超过1000亿的公司,用不到200亿就可以买到,这当然是桩好买卖。 如果说喜诗糖果是巴菲特投资理念转变后的小试牛刀,那么对可口可乐的投资则是经典案例。巴菲特将自己的投资理念变化归功于芒格的推动,但实际上这背后也反映了美国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商业模式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如果说工业革命以来,对有形资产(财产、厂房和设备)的投资定义了企业的价值,但从这时开始,这些让位于对无形资产的投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版权、商标和品牌。有形资产由实物财产定义,而无形资产由知识产权定义。由于会计准则植根于工业时代,根据会计准则,公司必须立即将所有的无形投资成本化,简而言之,对无形资产的投资不会增加公司的账面价值。尽管对无形资产的投资确实能增加公司的内在价值,但在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方法中并没有提到这些。 还是巴鲁克·列夫和阿努普·斯里瓦斯塔瓦两位教授指出,自1980年以来,美国公司投资于有形资产的资金逐渐减少,投资于无形资产的资金相应增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无形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超过了有形资产的增长率。 上述这些情况,对典型的价值投资者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投资于无形资产的公司必须从当前利润中减去这一成本,同时由于不能将投资金额计入账面价值,反过来又使得其具有高市盈率和高市净率的特征,这使股票显得很昂贵。但是,如果将估值方法从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转变为用调整后的现金流和资本回报率计算所带来的利润,那么从GAAP角度看起来昂贵的公司,实际上可能对具有公司股东心态的投资者而言,就具有了吸引力。 巴菲特看起来放松了对估值的要求,实际上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商业变迁。 第三阶段:从新经济模式下的网络效应中获取价值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他对苹果公司的投资。 巴菲特于2016年开始投资苹果,到2022年对苹果的持仓市值超过1200亿美元,占组合的比重达到40.76%。苹果也热切地回报了巴菲特,为他贡献了1000多亿美元的投资收益。在单只股票上赚取1000多亿美元,这也创造了投资史上的一个奇迹。 众所皆知,巴菲特一直给外界的印象是不愿意投资科技股,直到2013年芒格还说过,全世界都羡慕苹果的成就,但也没有比苹果更不符合伯克希尔想投资的企业标准的。他说,“我们真的非常讨厌必须要创造出全新的、创新的科技,还需要一个接一个不间断。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做不到苹果这样。所以我们也不会去试图进入苹果。” 没想到三年之后的2016年,巴菲特开始大举买入苹果。笔者在《财富善战者说》一书中概括了巴菲特买入苹果的几个理由:首先,苹果虽然具有很强的科技属性,但是它一定程度上是个消费品。其次,他运用菲利普·费雪的“闲聊投资法”,发现苹果的粘性极强。他带曾孙们去吃冰淇淋,看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部手机,年轻人的生活几乎全部围绕苹果手机进行,而一旦苹果推出新品,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更换。苹果公司拥有数以亿计有购买力的用户,他们可以用手机来交易、学习甚至做其它的事情,这俨然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第三,巴菲特非常欣赏苹果CEO蒂姆·库克,甚至不惜称赞他是“伟大的管理者”。他曾在2021年的年度信函中表示:“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将苹果产品的用户视为他的初恋,他的管理风格也让很多人受益。” 库克执掌苹果之后大力推动股票派息和回购。在过去三年里,这家科技巨头每年派息约140亿美元。苹果从2012年3月开始支付季度股息并回购股票。根据标普全球市场财智公司提供的数据,从那以后一直到2021年夏天,苹果已经在股票回购上花费了超过4670亿美元。回购可以减少公司的股票数量,从而提振收益和股价。这是巴菲特非常喜欢的一类投资标的。 苹果还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现金奶牛”。截止2022年第一季度,苹果拥有约2026亿美元的现金储备,远高于与科技公司谷歌(1692亿美元)和微软(1324亿美元)。充沛的现金是苹果可以实施大规模回购和现金分红的基础。所以,如果说乔布斯时期的苹果是一个科技成长型企业,而库克接管之后的苹果则进一步转型为了一家蓝筹股企业。 第四,巴菲特买在苹果的低迷时刻。表面上看2016年并不是什么好的时机。从行业角度,当时恰逢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到达行业天花板,行业开始进入下行的节点。而从苹果本身来看,此时乔布斯已经去世5年,苹果被批评为创意枯竭,当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业绩13年来首次下滑,营收下降13%,净利下滑22%。2016全年苹果年营收为2170亿美元,比前一年下滑9%。 但是巴菲特看到的东西不一样,2016年初,全球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上,苹果份额为62.3%,三星为22.1%。虽然创新不足,但是苹果的市场优势却在不断扩大。这说明通过多年的技术领先,苹果已经实现了可持续的垄断性领导力,它的护城河已经坚不可摧,而盈利的暂时下滑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买入时机。 《终极金钱心智》这本书则为巴菲特购买苹果公司增加了一个商业模式变化的最新背景。如果说巴菲特的第一阶段投资对应的是工业时代的厂房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第二阶段投资是从有形资产转向了对品牌、专利等无形资产,那么他的第三阶段投资则开始关注到了新经济模式下的网络效应及指数化增长。 苹果公司无疑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这符合第二阶段的特征, 同时苹果也是一只新经济类型的股票,苹果的所有产品和服务都使用了苹果的IOS操作系统,一旦产品成为苹果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网络效应就会形成,正向反馈、路径依赖和锚定效应等将创造一个强大的全球特许经营权,因为苹果客户的转换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网络效应背后则藏着旧经济与新经济的深刻分野。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指出,旧经济学更多地是基于物理学,其特征是“平衡”、“理性”,而在新经济学更类似于生物学,认为人是情绪化且不理性的,经济是复杂系统而不是简单系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不是静态的。 在以物理学为标准的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理论中,市场呈现出收益递减状态。收益递减定律是标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其内涵包括,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多增加一个因素,即要求,就会在某个时点上降低单位生产的增量回报。换句话说,收益递减定律是指达到某一点后,所获得的经济回报水平相对于所投资的资金而言,会下降。 然而,复杂经济学认为,有些公司注定不会受长期收益递减定律的影响。根据阿瑟的观点,有一些公司的经济回报会继续增长,他解释说:“加速回报,是指那些领先的会进一步领先,而那些失去优势的会进一步落后。”收益递减是旧的实体经济的一个特征,与此同时,“加速回报正在成为新经济,也就是知识型产业的特征。” 加速回报在网络效应常见的特定技术领域中尤为显著。网络效应是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某个产品或服务,其价值会有所增加的现象。所以在新经济条件下,一旦某个网络达到50%的市场份额,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坚不可摧的实体。创造数亿美元利润的公司往往能有数十亿元的市值,而推动这些所需的资本仅仅是工业革命时代所需资本的一部分而已。 巴菲特自己并没有从这个角度阐述过投资苹果的理由,不过哈格斯特朗还是认为对苹果的投资代表了巴菲特跨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投资价值的完美投资案例。 在2019年伯克希尔年会上,芒格指出,巴菲特愿意投资苹果对伯克希尔来说是一个好兆。芒格打趣道:“要么是你发疯了,要么就是你在学习,我更喜欢学习的这种解释。” 的确,永不放弃学习可能才是我们最需要向巴菲特学习的地方。哈格斯特朗也感慨,研究巴菲特的最大回报之一,是观察他作为投资者在过去65年里是如何发展的,从价值投资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现在再到第三阶段。“很少有投资者能从第一种方法进化到第二种方法,更不用说第三种方法了。要想在一个市场周期中取得成功,需要灵活的头脑、合适的投资气质以及持续学习的强烈愿望。这是金钱心智运作的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巴菲特60多年漫长职业生涯表面波澜不惊的背后实际上暗藏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惊人迭代进化,很多人批评他错过了新经济,实际上他并没有缺席任何一次重大的商业模式变迁,甚至比任何人都抓住了更多。 (舒泰峰 重阳投资合伙人,财经作家,著有《财富是认知的变现》、《财富善战者说》等) 向上滑动阅览【免责声明】
本材料文字及图片版权归原创方或原作者所有,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重阳投资”)转载文章已获原创方或原作者授权。
本材料内容仅代表原创方或原作者的分析、推测与判断,登载于此仅出于传递信息和投资者教育之目的,并不意味着重阳投资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也不代表重阳投资与原创方或原作者有任何代理或合作关系。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重阳投资不作任何明确或隐含的声明或保证,且不承担信息传递的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相关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广告、销售要约,或交易任何证券、基金或投资产品的建议。本材料内容中引用的任何实体、品牌、商品等不代表重阳投资的实际操作。因基金产品投资限制、投资组合调整和交易成本等多种因素,重阳投资的实际操作有可能与本材料中得出的结论不同。
本材料并不考虑任何阅读者的特定投资需求、投资目标或风险承受能力。阅读者在投资之前,应当仔细阅读产品法律文件和风险揭示书,充分认识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如您对重阳产品感兴趣。


(来源:重阳投资的财富号 2025-04-29 15:36) [点击查看原文]
郑重声明:用户在财富号/股吧/博客等社区发表的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视频、音频、数据及图表)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不对您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请勿相信代客理财、免费荐股和炒股培训等宣传内容,远离非法证券活动。请勿添加发言用户的手机号码、公众号、微博、微信及QQ等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评论该主题
帖子不见了!怎么办?作者:您目前是匿名发表 登录 | 5秒注册 作者:,欢迎留言 退出发表新主题
郑重声明:用户在社区发表的所有资料、言论等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不对您构成任何投资建议。用户应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自行决定证券投资并承担相应风险。《东方财富社区管理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