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曾在浙江萧山的乡镇机修厂里听过铁锤敲击的回响,就能想象 1970 年代鲁冠球面对万向节时的场景:昏黄灯泡、铁屑四溅,谁也不相信这个又脏又累、还赚不到几个钱的小零件会撑起一家上市公司的台柱子。可鲁冠球偏要把赌注压在最不起眼的“边角料”上,因为他笃定——等我国开始大规模造汽车,零部件品质迟早会决定整车厂的脸面。于是,一个农机厂的车间被改装成万向节实验室,萧山小镇也在悄悄酝酿一条环球底盘之路。
1994年深秋,万向集团把零部件业务剥离,组建“万向钱潮”并上市。那一声钟响不仅带来融资,更让一家乡镇工厂快速吸收现代公司治理——董事会引入外部独董,财务用起 IFRS 准则,供应商体系第一次被量化考核。资本市场像一把手术刀,把传统集体企业的“父子帐”切割得干干净净,也给后来所有民企描了一条“拆分上市”的样板曲线。
金豆每日会在蛐蛐TA小栈分享小故事,再继续聊~
................................................................................................................
金豆蛐蛐TA小栈
金豆刚毕业那年,我拿着三千块工资,日子虽紧,但挺踏实的。直到看到一个同学在大厂晒工牌、晒下午茶,我突然觉得,自己混得像个笑话。
其实我什么都没少,钱也够花,只是看到别人多,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少了。
这是“相对剥夺感”——不是你过得不好,而是你以为别人过得更好。你本来满意自己的小天地,但一刷朋友圈,世界突然按“别人”的标准重构了。人不是活在现实里,是活在参照系里。
经济学上说,幸福感取决于相对位置,不是绝对收入。这也是为什么你换了工作、涨了工资,开心几天就没感觉了——因为你总能找到“更厉害的那个人”。
如果幸福需要你赢,那你永远都输。先选对坐标轴,再谈什么“过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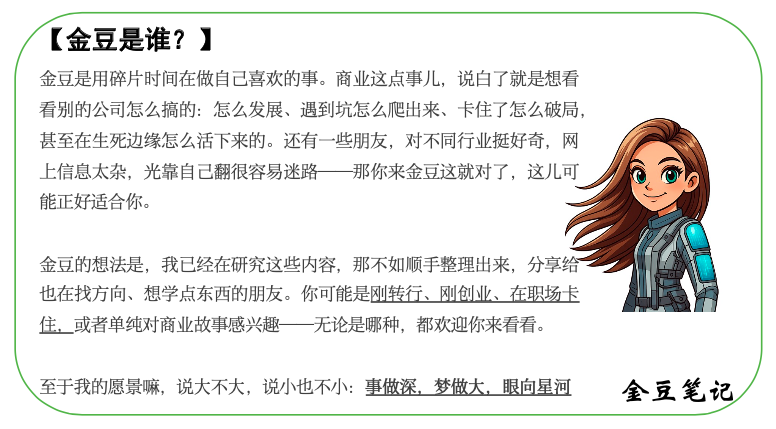
................................................................................................................
深井打法—只做底盘里的“隐形骨骼”
上市后,鲁冠球和团队没有去追风口造整车,而是把驱动轴、悬挂、制动、轴承这些“看不到 logo 的骨骼”越做越深。他们的逻辑很简单:
“车身外壳能打广告,但真正握在驾驶员手里的安全感,全靠底盘硬件。”
二十多年里,万向钱潮像往井里埋管子那样,把产品范围从轿车拓到 SUV,再到新能源车型;又像养藤蔓一样,把客户名单从一汽、东风写到宝马、特斯拉,海外营收在 2024 年已占到总盘子的三分之一。深耕路线让公司一度被投资圈称为“隐形冠军”,因为它站的位置,恰好是巨头看不上、散户做不透的夹缝。
走进车间,一颗球笼里的 200 项专利
如果你有机会站在杭州基地的等速驱动轴产线边,会看到高速旋转的球笼里刻着细密螺旋槽。那个角度并非美学设计,而是工程师用 6000 小时台架试验找到的最佳降噪曲线。类似的细节被写进 200多项专利,覆盖轻量化钢材配方、扭矩自动补偿、耐久涂层等环节。更关键的是,这条产线同时满足 TS16949、ISO14001 等多国标准,工人只需换一张标签,就能把同一根半轴发往底特律、慕尼黑或武汉。这样的跨标准制造能力,在零部件圈里并不多见。
时间跳到 2025年春天。新鲜出炉的 2024 年报显示: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8.68亿元,同比下降11.17%;归母净利润9.51亿元,同比增长15.76%;扣非净利润9.33亿元,同比增长21.6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13亿元,同比增长9.02%;报告期内,万向钱潮基本每股收益为0.29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0.65%。公司2024年度分配预案为: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1.8元(含税)
把镜头拉远—与全球巨头的身形对照
若把万向钱潮摆进全球零部件座次表,它还是“小个子”。博世 2024 年营收 905亿欧元,主业 Mobility 单元 alone 就跑出了 560亿欧元;大陆 397亿欧元,EBIT 稳在 6.8%;ZF 同期 414亿欧元,即便亏损,体量也足有它的三倍。国内同行里,华域背靠上汽市占率高歌猛进,拓普凭借轻量化方案利润涨到 30亿元以上。与这些“大体量+系统集成”玩家相比,万向钱潮像工匠:产品线单一却刻得深,品牌在北美有口碑,但在智能化、电驱集成上显得“慢半拍”。
真正的挑战发生在 2020年后。新能源车把传统动力系统一拆再拆,昔日“核心”的等速驱动轴可能被电驱桥一次性替代;整车厂还学苹果那套垂直整合,向零部件要更高集成度、更低成本。面对潮水,万向钱潮干了三件大事:在苏州和杭州新建数字孪生工厂,把良品率当 KPI;拉上宁德时代做电池壳体,把冶金积累嫁接过去;成立新能源动力总成事业部,研发轻量化半轴和一体化电驱动底盘。2024 年,新业务只贡献了不到 12% 的营收,但它们像新开的井眼,正在积攒流量。

万向钱潮没有特斯拉那样坐火箭,新闻热搜也常被更“性感”的智能驾驶公司占领。可每次聊到这家企业,我都会想起车间里那只被锤子敲亮的万向节:它在几十万次转动里守住了公差,也在工业周期的大起大落里守住了现金流。
制造业的未来当然需要算法、需要 AI,也需要高举高打的系统方案。但很多时候,一条产业链的韧性,恰恰来自那些愿意在“边角料”深挖到底的工匠。半世纪前,鲁冠球在铁屑里下注;半世纪后,万向钱潮还在底盘深井里敲梆子。故事没完,因为车轮还在转,井口也还在继续往下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