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央企背景上市公司,大唐高鸿暴露的内部问题并非孤立个案,而是呈现出系统性、家族化利益关联与链条化操作的特征,其核心根源在于权力过度集中、内控机制缺位及外部监管响应滞后。这些问题最终逐步侵蚀公司根基,对投资者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一、权力结构失衡:长期“一言堂”与治理机制失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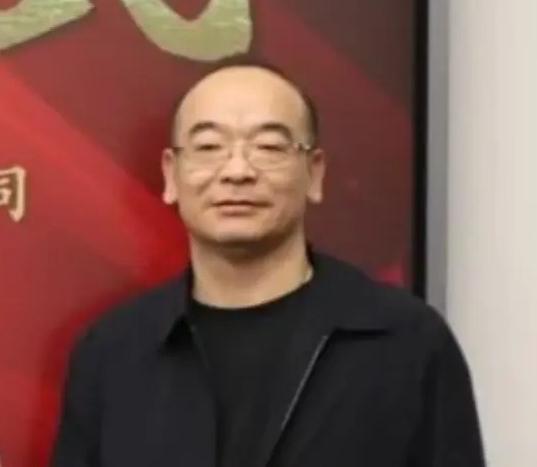
1. 22年任期下的权力集中:董事长身兼数职,决策缺乏制衡自2003年起,付景林长期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还兼任总经理,形成对公司的绝对主导权,直接干预董事会决策流程。
这种权力格局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形同虚设:董事会未能发挥实质监督作用,监事会未能履行合规核查职责,审计委员会也未起到风险预警作用。
典型案例为2019年一笔1.84亿元的苹果手机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履行审议程序,直至2021年才补充审批,反映出管理层对制度执行的忽视。
2. 董监高集体违规:9人参与操作,监督链条断裂据证监会调查,包括董事长、财务总监、监事会主席在内的9名董监高人员,均参与了公司的违规操作,形成利益共同体。例如,财务总监丁明锋直接负责虚假贸易的资金划转,监事会主席段茂忠签署不实审计报告,导致“决策-执行-监督”全流程的合规机制完全失效。
二、关联交易不透明:家族化利益网络与虚假贸易
1. “夫妻店”主导的贸易枢纽:南京庆亚的角色争议前董事曹秉蛟的配偶江庆控制的南京庆亚公司,是大唐高鸿虚假贸易的核心参与方。
2015-2021年间,该公司通过笔记本电脑“空转贸易”(无实际货物交割,仅通过单据流转),帮助大唐高鸿虚增营收185亿元,同时自身截留1.2亿元资金用于个人投资。具体来看,2020年一笔1亿元的虚假采购中,南京庆亚扣除500万元“服务费”后,仅向下游客户划转7500万元,最终导致公司实际损失800万元。
2. 多层关联嵌套:供应商、客户、物流的利益绑定虚假贸易背后存在多层关联方协作:
- 上游:南京庆亚指定的供应商多为曹秉蛟亲属控制的企业(如安纳佳、驰飞电子),通过伪造采购合同占用公司资金;
- 下游:南京贺坤、江苏农耕等客户的实际控制人韦光宗,与曹秉蛟存在密切关联,交易资金最终通过个人账户回流;
- 物流:合作物流公司配合伪造货物签收单,以“单据闭环”掩盖无实际货物的事实。
三、财务操作风险:虚增营收与资金使用违规
1. 虚假贸易的资金损耗:19亿“成本”与16亿资金占用虚假贸易不仅虚增业绩,还直接导致公司资金外流。
2015-2023年累计虚增营收198.76亿元期间,公司需向南京庆亚等第三方支付约10%的“协作费用”,累计损耗超19亿元。
此外,部分资金以“预付款”名义被关联方长期占用,截至2023年,被占用资金余额仍达16亿元。
2. 募集资金违规挪用:1.094亿未审批“补流”2024年,公司在未履行审批程序的情况下,将1.094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后续该笔资金流向关联方信安公司,被用于偿还借款及支付合同款。此举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反映出管理层对资金管控的随意性。
3. 内幕信息管控漏洞:高管增持与重组停牌的时间争议原股东陈俊举报称,2015年期间,公司股价暴跌时高管逆势增持,随后公司又宣布重组停牌(重组标的涉及南京庆亚),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操作。尽管证监会受理了举报,但公司未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暴露出内部信息管控的薄弱环节。
四、内控机制缺位:审计失职与流程空转
1. 内部审计形式化:应收账款风险与审批漏洞2023年内控审计报告显示,公司应收账款管理存在重大缺陷——1年以上逾期应收账款占比达71.46%,却未建立有效风险预警机制;此外,常州实道等重大诉讼涉及的《承诺书》,未经过董事会审议便签署,反映出授权审批流程的失效。
2. 外部审计核查失职:9年“标准意见”下的风险遗漏面对“高营收、低利润”“关联交易密集”等明显风险信号,审计机构连续9年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例如2020年,公司虚增营收占比达49%,但审计机构未对物流单据真实性进行穿透核查,仅依赖管理层提供的书面材料,未能发现核心风险。
五、不良操作风气:从制度缺位到全员惯性
1. 家族化利益关联的传导:“一人关联,多方受益”曹秉蛟家族通过南京庆亚、安纳佳等企业,形成“亲属+关联企业”的利益网络。例如,曹秉蛟之弟曹秉南持有驰飞电子22.5%股份,其配偶江庆通过南京庆亚截留资金,形成“一人主导,家族受益”的利益失衡生态。
2. 违规操作的惯性化:基层员工的“常规化”配合公司虽通过电子屏宣传“自由、平等、公正”等理念,但实际操作中,虚假贸易被部分员工视为“常规业务”,甚至主动配合伪造单据。例如,基层财务人员为完成业绩指标,参与虚构合同与物流记录,形成自上而下的操作惯性。
3. 举报响应机制薄弱:投资者诉求的“模糊回应”原股东陈俊因疑似内幕信息操作损失5800万元后实名举报,但公司未按规定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相关信息,仅通过投资者互动平台模糊回应,未能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切,也未能遏制不良操作倾向。
六、外部监管响应:滞后性与责任追究不足
1. 监管介入的事后性:从警示函到立案调查的6年间隔2019年,贵州证监局已就公司募集资金违规使用发出警示函,但未深入追查背后的关联操作链条;直至2025年,证监会才正式立案调查,逐步揭开系统性违规的全貌,反映出对长期风险的敏感度不足。
2. 责任追究的局限性:“重公司、轻个人”的威慑不足南京庆亚实际控制人江庆虽被罚款700万元,但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以公司处罚为主、个人责任追究为辅的模式,未能形成足够威慑力,难以遏制类似操作的重演。
七、治理漏洞的后果:退市风险与投资者维权
1. 强制退市与5.2万股东损失:欺诈发行的代价2025年,公司因欺诈发行、连续违规操作触发强制退市条件,5.2万户股东面临巨额损失。目前,投资者索赔诉讼已启动,预计涉及赔偿金额超10亿元。
2. 司法追责推进:部分高管面临合规风险北京公安经侦部门已针对冯鹏飞等高管的合同纠纷、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行为展开调查,涉案金额达3.5亿元;付景林、江庆等核心人员被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部分人员可能面临进一步的法律追责。
结语:
上市公司治理的核心启示大唐高鸿的案例,揭示了部分央企上市公司在治理转型中的核心矛盾:
传统“一把手”管理模式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冲突、监管穿透性不足与新型违规手段的博弈。要防范类似问题,需从三方面发力:
1. 权力制衡:建立董事长任期限制与独立董事提名机制,打破“一言堂”,强化董事会的独立监督作用;
2. 技术赋能: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交易数据全流程存证,减少单据伪造空间,提升内控透明度;
3. 监管协同:强化审计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连带责任追究,构建“穿透式”监管体系,提前识别关联操作风险。
当前,公司已进入退市程序,其能否通过重整重建市场信任,关键在于能否彻底切断利益关联链条、重塑合规治理生态——这不仅是大唐高鸿的考验,也是所有面临治理困境上市公司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