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国产替代的浪潮中,寒武纪们的崛起看似偶然,实则蕴含诸多必然。我们聚焦“国产替代浪潮中的隐形冠军”,本质上也是在聚焦那些深耕细分赛道的硬科技企业。
它们中,有的借天时地利人和实现业绩跃迁,成为产业自主的攻坚尖兵;有的在资本市场的估值重塑中,印证了硬科技“从研发投入到价值兑现”的逻辑,成为科技牛市的核心标的。通过研究这些典型样本,我们既能拆解中国科技企业从技术攻坚到资本突围的破局路径与成长密码,也能为市场读懂硬科技的长期价值提供参照。

曾经作为全球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图像传感器产业重要成员、亦是果链参与者而被外界熟知的韦尔股份,在2025年6月更名后的称呼,已正式改为了豪威集团。
2025年2月那场大佬云集的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豪威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虞仁荣受邀参加,并作为6位发言企业家之一、半导体行业代表就民营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和他一同参会的科技界企业代表,还包括小米集团雷军、宇树科技王兴兴等。
不过当时,他的头衔还是“韦尔股份”。
而“豪威”之名,源自2019年韦尔股份的关键战略并购:当时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北京豪威85.53%股权。而北京豪威的核心业务经营者,正是彼时在全球CMOS图像传感器领域极具竞争力的美国豪威——彼时该企业在全球CMOS图像传感器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三,仅次于索尼和三星,在消费电子、车载等场景已有一定程度的技术壁垒。
这次并购成为韦尔股份的业绩转折点,不仅让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净利润环比激增457.1%至3.3亿元,更重塑了原本依赖消费电子配套的业务结构,CMOS图像传感器业务迅速成长为营收支柱,为后续切入车载赛道、成长为“车载龙头”埋下关键伏笔。
无论是如今的豪威,还是曾经的韦尔,能在半导体赛道突围,核心离不开三个关键支撑:一是舍得在研发上下血本,以持续的技术投入筑牢硬实力内功,为产品迭代与场景适配提供底气;二是擅长通过并购等手段整合核心资源,像2019年收购北京豪威这样的关键动作,就快速补齐了技术短板并直接抢占市场份额,带来业绩;三是多线布局,在消费电子周期波动时提前押注车载赛道,成功培育出脱离消费电子周期依赖的第二增长曲线。
从消费电子“厂工”到车载视觉芯片龙头
过去数年,豪威集团的前身韦尔股份始终未能摆脱消费电子行业的周期性束缚,业绩随下游市场需求波动而起伏,估值长期被贴上“周期股”标签。而在智能汽车从“电动化”向“智能化”跃迁的浪潮中,视觉感知作为智能驾驶与智能座舱的核心入口,催生出千亿级车载芯片市场——这一趋势为豪威提供了突围契机,凭借并购积累的CMOS图像传感器核心技术与行业资源,公司从消费电子周期波动中走出,逐步成长为车载视觉芯片领域的核心玩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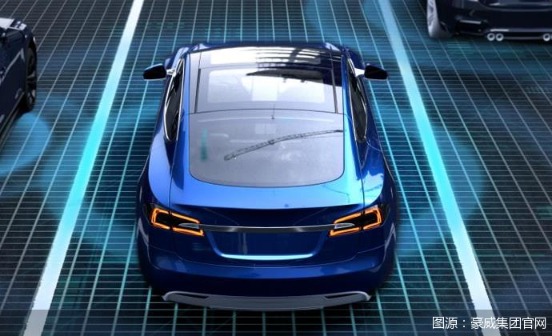
这种转型的关键价值,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向北京商报记者指出:“汽车业务占比提升,标志着企业从周期性较强的消费电子赛道,转向了高壁垒、长周期的车规级领域,而这一转向也成为豪威集团估值逻辑从周期股向成长股切换的核心驱动力量。”
业务转型的成效,首先体现在车载收入的爆发式增长。据韦尔股份2024年年报披露,公司核心业务板块“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中,来自汽车市场的收入在2024年达到59.05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29.85%,占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总营收(191.90亿元)的比例超30%,成为与智能手机业务(98.02亿元)齐头并进的另一核心收入来源,且增长率高于智能手机业务三个百分点。
作为较早切入车载视觉芯片赛道的玩家,豪威率先享受了智能汽车行业的赛道红利。群益证券研报指出,进入2025年,“智驾平权”已成为车载行业明确的核心趋势,比亚迪、吉利、江淮等主流车企纷纷推出相关战略——其中比亚迪尤为典型,其全系车型中占比超七成的20万以下车型将全面推进智能化升级,这一动作将加速L2+级智能驾驶的普及。从需求端来看,L2+智驾车型对摄像头的搭载需求较传统车型大幅提升,单车摄像头数量接近10颗,这不仅为摄像头模组、雷达等上游环节带来巨大增量空间,更直接拉动车载CIS(CMOS图像传感器)的市场需求。
作为国内车载CIS领域的龙头企业,豪威集团当前在该赛道的市占率已接近30%,且产品具备显著竞争优势:其车载CIS不仅分辨率高、传感器尺寸紧凑,还拥有更强的弱光环境适应能力与更低的功耗,能匹配不同车企的智能化车型需求。此外,公司在技术迭代上亦保持领先,2024年底推出的业界首款1200万像素车载传感器,进一步拔高了行业高端产品的技术标准,强化了自身在高分辨率车载视觉芯片领域的竞争实力。第一证券研报进一步指出,当前全球车载CIS市占率层面,韦尔股份销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安森美成为行业龙头。
业务增长的韧性也在财务数据层面得到印证——2025年豪威集团半年业绩预告显示,随着图像传感器产品在智能驾驶领域的持续渗透,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3.49%—15.97%,归母净利润增幅更是达到39.43%—49.67%,第二季度营收创下历史新高。这一表现不仅验证了车载业务的增长潜力,也为估值逻辑的切换提供了业绩支撑。
支撑这一转型的深层逻辑,在于智能汽车产业从“电动化”向“智能化”跃迁催生的结构性机遇。而业务结构的重塑还推动了盈利模式的升级,国际注册创新管理师卢克林向北京商报记者强调:“车载业务的成长属性并非天然成立,需通过业务增长质量与盈利稳定性来验证,只有持续实现高质量增长,才能让市场真正认可其成长价值。”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亦向北京商报记者指出,豪威当前采取的策略,不仅是其实现定位升级的关键,也为市场将其估值逻辑从周期股向成长股迁移提供了核心依据——这种策略既保障了产品的竞争力,也为盈利稳定性奠定了基础。
懂并购,另一种打法
2025年6月11日,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其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显示,在6月10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99.9035%的压倒性同意票。
这意味着,这家以半导体分销业务起家、市值曾一度突破4000亿元的芯片巨头,即将正式告别在A股市场使用了八年之久的“韦尔股份”之名,转而更名为“豪威集团”,全称则为“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这次更名并非临时起意,“豪威”筹划已久。2019年,韦尔股份完成了一次A股半导体发展史上经典的“蛇吞象”式并购。
根据当时的公告,2018年,韦尔股份的营收为39.64亿元,总资产46.00亿元,而被收购标的北京豪威科技,同期的营收为87.10亿元,总资产约87.98亿元,体量远超收购方。豪威科技曾是全球CMOS图像传感器领域的明星企业,1995年成立于美国硅谷。作为苹果早期的供应商,它曾因iPhone 3GS和iPhone 4的成功而声名鹊起。但自2011年苹果iPhone 4S将主摄像头订单转向索尼后,豪威科技逐渐失去了消费电子领域的顶端光环,但其技术底蕴和市场地位依然稳固,始终位列全球CIS市场前三。
除了业务开拓与技术进取,擅长并购成为韦尔股份身上另一个鲜明标签,且其并购策略向来精准,始终围绕产业链补位展开。
公开资料显示,在2013年、2014年以及2015年,韦尔股份先后收购了三家公司。在2019年吞下比自己大5倍的豪威科技后,韦尔股份又看上了思比科等企业。
买了思比科,便补上中低端图像传感器产品线;2019年收豪威,直接拿下全球高端CIS核心技术和客户网络;2020年从Synaptics收购了TDDI业务,切进显示芯片;2023年收购芯力特、芯测半导体,补上模拟芯片和封测能力。
既有底层技术迭代能力,也有市场布局整合能力。技术是护城河,并购给它增长空间。过去多年,这家公司也在“技术—资源—场景”之间,不断重构自己的能力边界。
从“韦尔”到“豪威”,有钱还是缺钱?
2025年6月,更名完成后的豪威集团迅速递表港交所,开启了港股IPO的进程。两个月后集团便收到了来自港交所备案反馈,被要求重点说明“控股股东认定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及“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具体情况及其对控制权的影响”——实控人虞仁荣的高比例质押,或被认为已威胁其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据豪威集团2025年8月21日最新公告,虞仁荣持有公司3.33亿股股份,占总股本27.65%,累计质押1.78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达53.51%,占公司总股本14.8%,其中部分质押用途明确为“偿还借款”,这一质押比例在申万半导体行业165家A股上市公司中位列第二,结合港交所相关上市规则中“发行人需证明控股股东具备持续控股的财务能力”这一要求,虞仁荣若无法合理解释高质押下的资金用途及财务稳定性,或将成为港股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若上市公司实控人质押股份比例超50%,要注意质押风险问题。如果后续公司股价下跌,金融机构还可能要求追加担保,一旦质押比例继续走高,其中的风险也会越大:“半导体行业属于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壁垒也较高,如果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率接连走低,可能让公司面临未来市场份额流失等风险。”
与港股上市争议相伴的,是豪威集团在A股市场股价表现与半导体板块行情的显著背离。2025年以来,A股半导体板块在国产替代与需求回暖驱动下持续走强,4月9日—8月28日的98个交易日内区间累计涨幅达51.12%。本该迎风向上的豪威集团同期股价却仅上涨24.09%,跑输板块超27个百分点,截至8月28日公司股价收于142.89元/股,总市值1723亿元位列板块第五。
对于这种股价背离,郭涛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这种差异或许可以被视作估值逻辑切换的阶段性体现。一方面豪威虽实现业绩增长,但消费电子周期影响仍在,叠加实控人高质押、研发费用率下滑等风险,市场对其从消费电子向车载芯片切换的定位尚未形成共识;另一方面,全球车载CIS市场竞争格局复杂,投资者对豪威长期市占率保持观望,业务成长性的不确定性直接反映在股价上,导致公司未能充分享受半导体板块红利。”
作为技术密集型企业,豪威集团的研发投入情况直接关系其在车载CIS等核心赛道的竞争力,但相比早年的“舍得”,现在的豪威集团有些“手紧”。
2022—2024年公司研发数据呈现“费用波动、费率下滑”的趋势,与车载芯片“高研发强度”的行业特性形成鲜明反差。
具体来看,2022年公司研发费用为24.96亿元,2023年降至22.34亿元,2024年虽回升至26.22亿元,但整体看未能保持稳定增长;研发费用率则连续三年走低,2022年为12.43%,2023年降至10.63%,2024年进一步降至10.19%,且2024年在营收同比增长22.41%的情况下,研发费用同比增幅约17.37%,未能与营收增速同步。
针对研发投入的问题,卢克林向北京商报记者指出,车载CIS技术迭代速度极快,豪威目前虽领先行业,但研发费用率下滑可能影响后续技术储备,长期将削弱产品竞争力。研发费用率与豪威“车载芯片核心玩家”的定位不相匹配,难以支撑估值,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其长期成长性的疑虑。
另一点同样值得关注——与研发费用率持续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豪威集团董监高薪酬在2024年逆势大幅上涨,且在实控人“质押还债”的背景下,形成了显著的资金分配悖论。从薪酬数据来看,2023年公司董监高薪酬总额为883.88万元,2024年增至1240.81万元,同比增幅超40%;其中,董事仇欢萍年薪从21.52万元大涨126.18万元至147.7万元,董事吴晓东年薪从182.92万元上涨104.22万元至287.14万元,董事长虞仁荣年薪更是从111.16万元翻倍至226.69万元。
同期,2024年豪威集团还分红5.04亿元,其中虞仁荣个人获分红约1.69亿元,其本人及一致行动人还捐赠6060万股(市值约61.72亿元)用于教育事业。
一边是实控人质押股份偿还借款,一边是高额捐赠、分红与董监高薪酬大涨,这种资金分配悖论,不仅导致薪酬增幅远超研发投入增幅,若不能与研发突破、技术领先性挂钩,将进一步损害市场对公司的信任。北京商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尝试与豪威集团取得联系,截至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复。
尽管豪威已成长为车载CIS领域的龙头,但行业竞争与自身发展的挑战仍不容忽视。郭涛向北京商报记者提及:“巨头及大量车企自研团队仍在智驾领域加速渗透,豪威要巩固成长股定位,还需持续满足一系列核心验证方向:比如汽车业务增速能否跑赢行业平均水平、高毛利智驾相关业务占比能否持续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能否维持行业领先等。这些维度的表现,将直接决定其能否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